《天坛新六十记》
我写天坛,不仅仅是写天坛之景,更多的是写天坛里的芸芸众生,写天坛作为皇家的祭坛,是如何演进并演变成为人民的园林的。在这种由时代所演进和演变的历史进程和背景中,不仅有天坛空间对于普通百姓一步步的开放,还有人对时间和空间新的利用、占有和定义。也就是说,在这样的人与时间、空间三位一体的纵横交错和相互作用中,书写天坛和芸芸众生尤其是和北京人如今的密切关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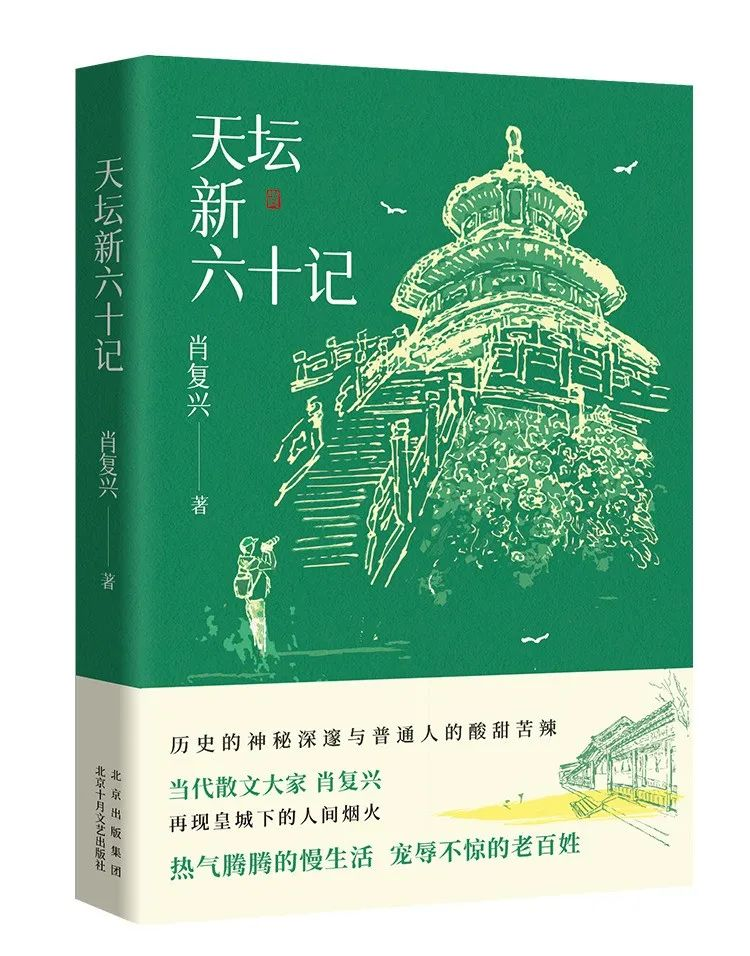
《天坛新六十记》
肖复兴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《天坛新六十记》并不是介绍天坛历史或书写天坛风景的导览之书,而是作者借在天坛写生的机会,贴近公园里的普通百姓、平凡草木,将来往于此的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、人生际遇,一一记录,构成一幅当下市民生活百态图。
我的上一本书《天坛六十记》,是2019年8月初到2020年1月初写成的。写完这本书之后,去天坛的当天晚上,在电视上看到钟南山,知道武汉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,便一直宅在家中。再去天坛,是四个月后的4月底,已物是人非,心情迥异,只有天坛处变不惊,依然如故,辉煌的祈年殿巍然矗立,阅尽春秋,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这些芸芸众生。满园的二月兰正在怒放,挥洒着一地绚烂而坚强的心情。看到这一切,我感到震惊,忽然觉得,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导师;天坛是让我们时刻记得,这个世界上有值得我们警醒和参谒的高处。
回到家,我写下了一则感想。当时,并没有想到可以接着《天坛六十记》,再写一本新书,只是写得渐多,算是聚沙成塔,时间的馈赠吧,才萌生了续写一本《天坛新六十记》的想法。
因家离天坛不远,退休之后,无所事事,我常到天坛来。起初来天坛,不为写文章,只为画画,散散心,消磨时光。没有想到,你画画,会有人看画,由此而来,又会有人和你说话。即使画得再不成样子,画居然也意外地成为一座座小桥,沟通了彼此的往来,似乎大家都不希望孤独,而渴望交流。陌生人之间,擦肩而过是一种形式,相互交流也是一种方式。
忽然发现,如果说天坛像一方舞台,演出的绝对不是哑剧。众多的游人,尽管素不相识,如同来自不同地方各自独立的一颗颗水珠,但天坛却像一泓清泉或一条河流,让这些水珠在这里流淌、交汇、碰撞,单独的水珠和水珠之间,便有了奇特的交融。在画画中,我结识不少人,听他们聊天,与他们交流,便是这样的交融方式的一种。不由得扩大了我的视野,蔓延出我的心际,时有收益,便有感而发,随手记一点笔记,属于搂草打兔子,让单薄的画多了一些内容或画外音。我戏称之“画为媒”。
《天坛六十记》就是这样写成的。《天坛新六十记》也是这样写成的。只是,前一本写了半年,这一本从2020年4月底到2022年10月底,断断续续,不紧不慢,写了两年半的时间,文字比前一本多了三万余字。一册册拙劣的画本,如同一个个水罐,虽是浅浅地却也清澈地盛放着这两年半的时间,和时间里曾经荡漾着的活生生的人与事,情和景,思及悟。
望着天坛苍郁森森的古柏树林,望着祈年殿汉白玉栏前阶下的广场,望着丹陛桥上由低到高长长的御道,让我感慨无尽的时间,在这里如水一样流逝,又回溯流淌到我的脚下。在它们的面前,人是多么渺小,如芥如尘,而天在这里被作为祭拜的神一样的存在,是多么又高又大,又无边无际。
我写天坛,不仅仅是写天坛之景,更多的是写天坛里的芸芸众生,写天坛作为皇家的祭坛,是如何演进并演变成为人民的园林的。在这种由时代所演进和演变的历史进程和背景中,不仅有天坛空间对于普通百姓一步步的开放,还有人对时间和空间新的利用、占有和定义。也就是说,在这样的人与时间、空间三位一体的纵横交错和相互作用中,书写天坛和芸芸众生尤其是和北京人如今的密切关系。在这样如丝似缕密织一起的关系图谱中,有上一代人的回忆,有新一代人的心绪;有时代的倒影,有历史的叙述;有现在进行时态的跌宕起伏,也有我自己所思所想所忆中雪泥鸿爪的痕迹。即便绝无消息传青鸟,却也衬出春心带草痕。
是的,天坛只是背景,并不是主角,来天坛的这些普通百姓才是主角。我的书中主要写的是他们。他们给予我很多,让我面对天坛,那样的感动和感喟;让我在写作《天坛新六十记》那两年半时间里,过得自以为充实一些。
我的一位远方的朋友写的一首诗中说:
世界仿佛不只有田野,
还有故事。
我可以说:
世界仿佛不只有天坛,
还有故事。
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写的一首诗中说:
公爵的身后是一个宗族,六翼天使身后是大众,每个人的身后都有数千个和他一样的人。
我可以说:我在天坛遇到的每一个人的身后,都有数千个和他一样和我一样的人。在祈年殿的身前身后,是这样数千数万大众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他们和天坛才匹配,没有了他们,再伟岸的天坛,也只是一座空坛,只存在苍老的历史,没有新鲜的生命。书写他们,其实就是写我自己,写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。天坛,只是存放这些人这些故事这些心绪的一方圣坛。
在写作方式上,我依然坚持的是前一本《天坛六十记》的原则,即布罗茨基所强调的那种创作原则:“意识中所产生的自然法则。”“也可以这么说,这是粘贴画和蒙太奇的原则。”他同时强调说,这是“浓缩的原则,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倘若你开始用类似浓缩的方式写作,全都一样,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写得都很短”。对于如今被资讯焦虑与生活快节奏所簇拥裹挟的读者,布罗茨基一言以蔽之:“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。我们大家都知道,现代人所谓的attention span(意为一个人能够集中注意力于某事的时间)都极为短暂。”我深以为然,一直坚持,因为我知道,大多数人的阅读,已经没有那么长久的耐心。
同时,书中加入了我画天坛的一些画,虽然画得不好,却也是一份心情,是这两年半去天坛时的一点收获,是天坛给予我的一份难得的馈赠。
希望这本《天坛新六十记》,比前一本《天坛六十记》写得多少有些进步。即使写不成天坛的交响,起码是一支回旋曲。
本文首发于《中国青年报》客户端,摘编自《天坛新六十记》一书自序。作者系著名作家,已出版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报告文学集、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一百余部,近著有《我们的老院》《北大荒断简》《天坛六十记》等。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