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
近日,著名作家肖复兴新作《天坛新六十记》面世。天坛曾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的地方,现如今却是普通百姓游玩的打卡胜地。今天起,我们陆续连载《天坛新六十记》,邀请读者朋友们一起领略皇城下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。
春天早晨的诗
春天的早晨,天坛里的空气格外清新,松柏古树散发出的气息,是在别处闻不到的。这种气息,带有时间穿越而来和岁月沉淀之后的负离子,一般杨柳之类年轻树木的气息,是无法与之匹敌的,甚至开花树木的芳香也无法相比。弥漫着这种得天独厚气息的公园,只能是天坛。
这时候,来天坛的老人居多,老人和古柏那样地契合,摇曳着的青青的柏叶,是白发银须的另一种形态。这些老人大多在锻炼身体,也有穿着漂亮的春装跳舞的,多是女人。跳舞,也是锻炼的一种。
我坐在丁香树丛的长椅上,翻看一本《英国诗史》。这是一本1997年出版的老书,看它,并非为了解英国诗歌的历史,只是临出门前随手带上的,走累了,无聊时,翻翻而已,就像老人出门时随手带上的一根拐杖。
每一株丁香树下,都挖成一个四四方方的浅坑,是在培土,准备浇开春的返青水了。新鲜的泥土,像新生婴儿一样清新,即使黑色,也黑得油亮,湿润。丁香花开的日子还要等一个来月,花开的时候,这里一片花海,香味浓郁得像长上了翅膀一样四处乱窜,来拍照的人很多。丁香树的花开和凋零,是完全不一样的,如果叶子都落光,枯枝散漫如乱发,摇响在凄清的寒风中,更是不一样的风景。那时候的丁香树灰头土脸,像土拨鼠,很有些丑陋,让你想象不出它们也曾有过花开青春季节的辉煌,让你感慨老去时的苍凉和无奈。树的四季,其实就是人的一生。只不过,树可以轮回。
这时候丁香树虽然还没有开花,却已经有点儿绿叶了,正在做青春返场大戏前的热身。微风温煦,人又少,很清静,最适合坐在这里,愣愣神。有本书陪伴,随便翻翻,更有一种红袖添香般的惬意。我想,这不仅是我,也是不少读书人最浅薄的自我安慰吧。想想一冬这里都没有坐过包括我在内的一个游人,会惭愧自己的冷漠和忘恩负义,那么快便忘记了这里曾经花开如海的烂漫。
这时候翻书,颇似占卜,随手翻到哪页便是哪页,看看这一页说的是什么,和自己有什么联系,冥冥之中如古人神谕一般,给人某种神秘莫测的隐喻或暗示。特别在天坛看到这样的诗句,更会觉得有如某种从天风浩荡中传来的上天的旨意一般,让你有一种在别处难以体会得到的阅读快感和领悟。

这一天早晨,我随手翻到的是这本书的第171页,介绍弥尔顿的长诗《失乐园》中的一小节,是夏娃在伊甸园里的一段深情告白。其中有这样几句:
早晨的空气好甜,刚升的晨光好甜,
最初的鸟声多好听!太阳带来愉快,
当它刚在这可爱的大地上洒下金光,
照亮了草、树、果子、花朵,
只见一片露水晶莹……
《失乐园》,只是听说过,从来没有读过。现在,我对一切长的东西,都有些望而生畏,失去了耐心,更缺少了好奇,想来确实是人老了。翻到这一页停下来,主要是看到了“早晨的空气好甜”这一句,和此时的早晨情景那样吻合,完全是望文生义,并非真的看懂了这几句诗。弥尔顿说“早晨的空气好甜”,还说“刚升的晨光好甜”。我能感到空气好甜,却没有感到晨光也好甜。晨光,也能够好甜吗?这是诗人的语言。所以,我成不了诗人。
读完这一节诗,不知为什么,忽然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。
他是我北大荒的一位荒友,比我晚回北京好几年。1974年春,北京到北大荒招收高中毕业的北京知青回北京当中学老师,那时候,他是可以和我一起回北京的。他也是高中毕业生。可是,他没有报名。我知道,他有一个女朋友,是北大荒当地的人,被称为“柴火妞”。但是,柴火妞和柴火妞不同,他的这位柴火妞长得很漂亮,那些自以为长得有些姿色的女知青与之相比,也是相形见绌的。这是让他最动心,也是最割舍不下的原因。我离开北大荒的前一夜,大家聚餐,为我送别,他喝醉了。
知青大返城,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在1978年之后。绝大部分的知青都陆续回城了。他没有。并不是坚守以前那种“扎根边疆”的雄心壮志,而是为了爱情。有不少朋友嘲笑他:什么爱情,就是看中了人家的脸蛋儿,走不动道儿了呗!他不以为然,爱情之中,难道没有爱美这一项指标吗?一见钟情的情从哪儿来的?很多还不是先从脸蛋儿的美来的吗?这是他的爱情与爱美相互关系的哲学。
大多数知青都回到北京,一时待业在家,都开始忙着找工作,找房子,好安稳落脚,大家和他联系少了。两三年过去了,大家以为他肯定和人家结婚,没准小孩儿都有了。可是,就在某一年的冬天,他独自一个人回到北京。大家才知道,他没有结婚,不是他不想结婚,而是人家坚决不和他结婚。别看人家是个柴火妞,泥人也有个土性,主意大得很,不像有的柴火妞一门心思想进北京,匆匆忙忙嫁人,结果人到了北京,户口落不上,工作找不到,房子又没有。她不想过这样狼狈不堪的日子。她说她认命,是什么虫爬什么树!我见到他时,他这样对我说。说得很是无奈。
算一算,从那时到现在,我已经有四十来年没有见过他了。只知道他一直没有结婚,曾经有好多知青朋友,给他介绍丧偶的或离婚的女知青,知根知底,人都老了,脸蛋儿都皱成了枯树皮,还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?起码可以搭帮过个安稳的日子,何必自己苦自己,一个人孤灯冷灶地过这样凄凉的日子?他都没有同意,一直就那么单着。想想,刚返城那会儿,他还不到三十岁,现而今七十都过了,人生再长,也没有再一个四十年可过了。
知青的爱情,是知青人生的一部分。在上山下乡的历史大背景下,知青人生命运的轨迹基本相似,但爱情却不尽相同。如我的这位朋友,在知青的爱情故事中,虽然是极个别的,但是,其悲伤和无奈中所隐含的,不仅有时代的气息,也有爱情最宝贵的信息,便是爱情的真诚如一。尽管有些老掉牙,如一个过时的童话,但应该有一定的爱情的要义与本质在吧,或者说应该是爱情的一种吧?在世俗的社会中,这样的爱情之义和爱情之举,却变得稀少,甚至变质变味了。和如今天坛里相亲角那些纸牌牌上明码标价写的物质要求相对照,再想想如今婚配流行的说法:有车有房,父母双亡,实在让人感叹。我的这位朋友这种“望夫石”式近乎偏执的固守,即便有些可悲,却也有些我们如今自愧不如的东西。
弥尔顿在这一节诗的最后,还有夏娃对亚当告白的这样几句:
但是早晨的空气也好,
鸟的欢歌也好,
可爱的大地上刚升的太阳也好,
带露的草、树、果、花朵也好,
……
没有你,什么也不甜蜜。
对照这一节诗的开头,“早晨的空气好甜,刚升的晨光好甜”;最后弥尔顿写道,“没有你,什么也不甜蜜”;如此悬殊的对比,让我的心头一震。这一震,并不是为弥尔顿,而是为我的这位朋友。
“没有你,什么也不甜蜜。”还会有人相信这样的诗句吗?不少人转身换装一般,早已经换上了“缺了穿红的还有挂绿的”的流行小调了。
推荐阅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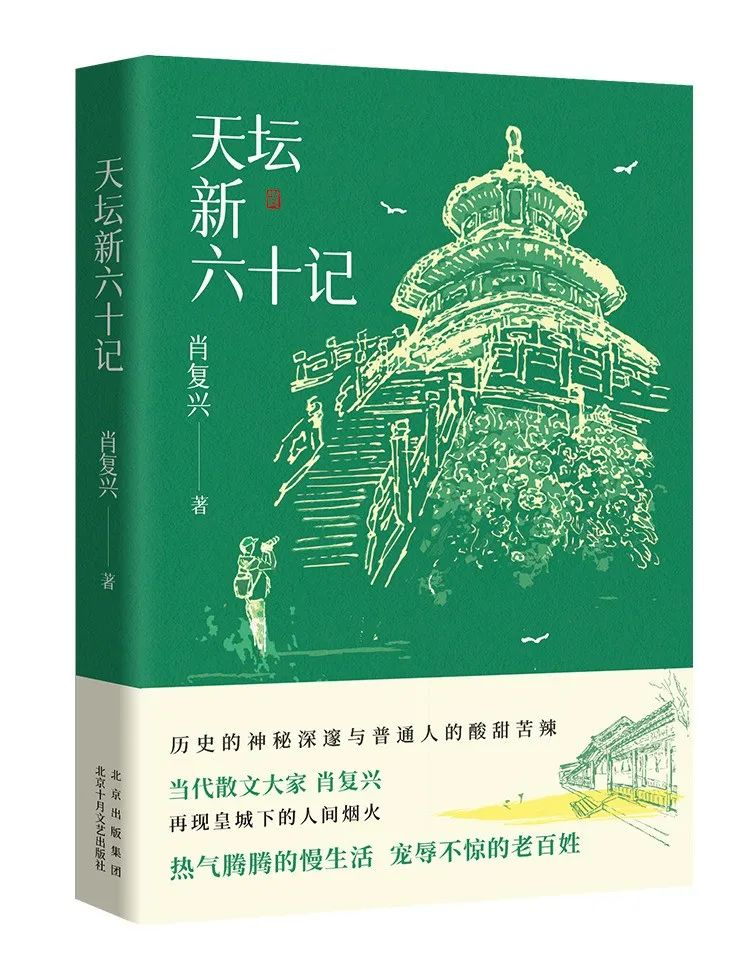
《天坛新六十记》
肖复兴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肖复兴,北京人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在北大荒插队六年,在大中小学任教十年。曾先后任《小说选刊》副主编、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、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、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。著有各种杂书百余部。曾获全国、北京和上海文学奖及中国好书奖、冰心散文奖、老舍散文奖、朱自清散文奖。
本书并不是介绍天坛历史或书写天坛风景的导览之书,而是作者借在天坛写生的机会,贴近公园里的普通百姓、平凡草木,将来往于此的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、人生际遇,一一记录,构成一幅当下市民生活百态图。










